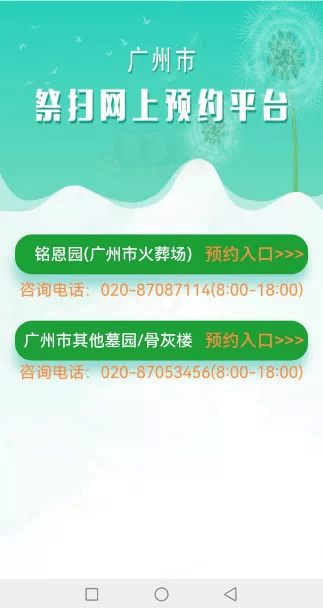New Wave这一阵是真又回来了,对于听歌习惯不同的人,“这一阵”代表的时间各有不同,有的是几年前,有的是几个星期前,或早到Franz Ferdinand发第一张专辑并且疯狂揽下各个巧立名目的音乐奖的时候,或到新裤子这张新专辑发行的十一黄金周,对于另外一些人,估计要等到SHE发下一张专辑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甭管怎么着吧,反正迪斯科蹦蹦蹦蹦的节奏又开始——或者要开始——满世界响起来了。
New Wave是火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年轻人们基本上玩腻了朋克,就开始弄出这种蹦蹦蹦蹦的鼓点,跟着乱扭起屁股来了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从朋克到New Wave,其音乐性的过渡是经过了一个后朋克运动,这个运动动静不大,因为它只存在于音乐上,不存在于行动上,而且也不是流行音乐,既没让人揭竿而起也没攻占唱片市场。反正曼彻斯特青年Ian Curtis最先把朋克音乐变化不大的乱七八糟三和弦改成了变化更小的蹦蹦蹦蹦和无尽重复的吉他扫弦,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暗黑灵魂。把暗黑灵魂表达得差不多了之后,Ian Curtis自杀了,Joy Division剩下的那哥几个就重组了个乐队叫New Order,这应该算是New Wave祖师爷了吧,1980年的事。
New Order的贡献是把Kraftwerk发明的电子合成器音符放进了他们自己的流行歌曲里,听过Kraftwerk的都知道他们作品里那种冷冰冰的美丽的电子音符,没有实打实的乐器,都是靠合成器和电脑完成的,不过New Order把这种东西放到蹦蹦蹦蹦里之后,他们就火透了,效仿者众,New Wave的第一春出现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New Order最先创造了快乐的迪斯科,跟着起舞就是那个年代最酷的事情。New Wave和Post Punk在和弦走向、扫弦方法、鼓点什么的音乐性上几乎没什么分别,但Post Punk阴沉黑暗,而New Wave开心乐天,这通过旋律走向区别开来。因为下行的旋律显得很颓,而上行的旋律比较上口,比较积极振奋,比较容易让人记住。比方说周杰伦《听妈妈的话》里“他们唱的都是我写的歌”这句,最后“我写的歌”就是个上行旋律,我敢肯定你在还没学会整首之前随口哼唱的时候,这句话是最先蹦出来的。New Order就把Post Punk里颓丧的一面都通过上行旋律弄成了乐乐呵呵的一面,顶多兑上点大众能接受的小哀伤。New Order是继承了一点Joy Division的低调气质,但如果说Joy Division是阴郁的话,那么New Order只是忧郁而已。反正,Post Punk相对比较不那么大众不那么日常一点,而迪斯科的New Wave则是流行消费品。
一夜之间滥大街的时髦玩意儿对于在它们流行之前已经形成价值观的人眼里当然太傻气了,就像现在35岁的人不容易喜欢周杰伦一样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在40后作家村上春树眼里,New Wave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Converse牌白色旅游鞋,上身一件带有“Genesis”字样的运动衫,挽至臂肘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鲁亚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猫王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猫王。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 & 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的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我同意道。
村上春树对他三十岁时流行的东西总感觉很怪异,那都是需要他主动作出理解努力才能顺顺当当接受的东西,而非显而易见、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东西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以下这段话也可以狭义化和低级化到他对流行事物的看法上:
“他一直对将有什么消失这点耿耿于怀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其实何必那样呢?任何东西迟早都要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当中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消失。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该消失的时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时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将长大成人。再过两年,这身漂亮的连衣裙就要变得不合尺寸,对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陈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么风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随波逐流,想也无济于事。”
事实上,New Wave风光了几年后确实就像一切流行风潮那样消失了,简直像夹着尾巴逃跑一样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用“傻气”两个字形容New Wave实在非常合适,因为迪斯科本身确实太傻气了,瞎蹦乱跳扭屁股就是当时人们满足的顶点,毫无可称之为内涵的东西。
我有这么个观点:一个流行风潮第一次产生和第一次消失的时候,它只是个流行风潮,而当一段时间之后它再次重现,而且这次并不像当年那样来得快死得猛,而是在世间万物中拥有了一个偏安一隅的心态和固定的或大拨或小撮的追捧者后,它就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点文化意味了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比方说运动鞋这个东西,无论《Size》、《鞋帮》等杂志办得多么风风火火,无论程旸等鞋评人多么努力描绘,我始终觉得目前的运动鞋没什么文化可言,它只是流行风潮而已,可能五年后,NIKE再发布一双鞋的限量版时,东方新天地门前决不会有人凌晨起来排队取号购买,而那之后再过十年,运动鞋风尚重新袭来,它才可能被称之为“鞋文化”,而程旸等人到那时才是真正在某个实在的领域有实在话语权的权威。
而New Wave的重新袭来,除去与之联姻的Synth Pop本身具有的、这些年来被忽视的美学意义之外,又有什么文化可言呢?我们先不用文化这么大的提法,但它肯定有值得被分析的地方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在80后作家、村上春树拥趸、乐评人祁又一的一篇关于新裤子《龙虎人丹》的评论里有这样的话:“新裤子的牛逼之处在于他们用不动感情的方式动感情……(新裤子)用反文化的方式搞文化建设,他们什么都不说,用最二最没大脑的方式把那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铺在地上,你可以觉得他们在开玩笑,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New Wave再度风行的要义所在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部分年轻人能代表的年轻想法(目前尚不能说是“进步想法”,但现在看有这种可能)正在通过网络占据主流话语权,虽然生于50年代的王朔早就有这些观点,但得到不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的广泛同意和支持,却靠上了8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种想法可以这样大致描绘:基本上反对被体系化和贴标签,基本上反对某个侧面的过度张扬,基本上反对道德上的价值评断。这样的想法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情况时,零落地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知识分子不可取,文艺气息不可取,小资心态不可取,小农心态不可取,感伤忧愁不可取,壮怀激烈不可取,道貌岸然不可取,流氓做派不可取……好吧,如果姿态都不可取,那我们还需要某种姿态吗?结果在日常消遣——流行音乐——上,我们的姿态借由三十年前的迪斯科舞步表示出来,指向了New Wave的单调鼓点、狂欢气氛,就成了新裤子“嘎巴嘎巴嘎巴嘿,嘎巴嘎巴嘎巴嘿”,成了“用不动感情的方式动感情”。New Wave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可以超越它初生时纯粹的、正面的、无需转弯的取乐工具,成为一种形式上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单调而强劲地二逼呵呵的节拍、流行旋律)反姿态的姿态表达器。
这就是New Wave三十年后超越性的意义和复生的理由所在,即其形式感恰好暗合了现在某种人群愿意持有的时代精神——如果可以用这种傻气词汇的话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
当然,为区区流行音乐的一个区区流行趋势扯上这么一大堆道理本身,也是很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可体系化的傻气工作总是有人要做,因为现在还看不到废除体系化的必要性我的世界末地门怎么做手机版。即使这工作做得非常幼稚而惹人发笑,也不能讳疾忌医,投靠一辈子郝舫、颜峻和李皖吧。
2006.10.22